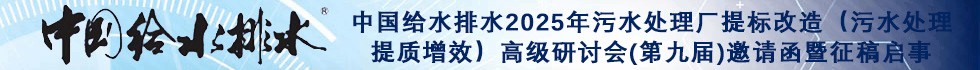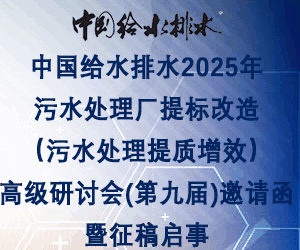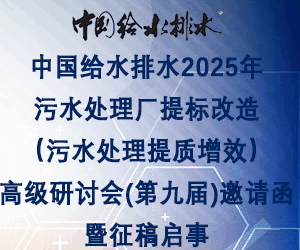来源:环保产业别册—《还原一个真实的宜兴环保产业》
1976年1月,宜兴召开了历史上第一个产品技术鉴定会,举办鉴定会的是高塍公社农机厂,农机厂的厂长一年多前,在上海遇到了同样是高塍籍的工程师,姜达君,姜达君当时只是想用自己的技术和工作的便利为家乡做贡献,他们共同开发了新型的PVC材质的纯水离子交换柱,一年多后,他们为新产品的成功开发,鉴定会的成功举办而欣喜不已,但他们没想到,这个召集人员多达数十人的“鉴定会”,产生了2800元的招待费,农机厂的相关领导一连写了5次检查放得过关,但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姜达君和农机厂因为这次不起眼的技术开发,他们的名字会长久的出现在记录宜兴历史的各个场景,其中5次检查,和2800的招待费用都详细的记录其中,但这段历史的条目却是:宜兴环保产业的起源。
应该说,这次的科研行为,犹如一颗在春雨前埋在沃土中的种子,注定要成为参天大树;随后发生的故事,犹如一场精心安排的戏剧,使我们再去探寻那段历史,即使已过了三十多年,仍然觉得目眩神迷。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我们这代人,只是上学时背到郁闷的政治考题,在那个年代,却开启了一代人的梦想;在江南,已经沉郁多年的商业文化,在人们的血脉中再次复苏;开发出纯水设备的宜兴人,这个时候等来了一个仿佛为他们而准备的机会。
1978年,全国人民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字句,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的宪法中,也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转批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第一次明确了中国要发展不要污染的理念;1979年,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部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试行)》。就这样,中国的环保产业,在懵懂中踉跄起步,同样开始起步的,还有在宜兴的那群人,1979年,依靠纯水制备而设立的宜兴县纯水厂,开始涉足工业废水处理领域,产值几乎年年翻番,而此时,姜达君的历史使命仍在继续,他的一位表弟王盘军和村书记谋划开一家村办企业,姜达君这次给他的是冷却塔填料,并以此创建了宜兴县太滆建设设备厂,这家厂和宜兴纯水厂,可以称为宜兴环保产业的两所黄埔军校,现在高塍所有的企业都和这两家企业或多或少的有些渊源。1980年,在高塍的环保产业达到了32个,而到了1983年,纯水厂和设备厂就分别衍生出22个和19个企业,高塍的环保企业也快速发展到79个。
1986年到1990年,是大家公认的中国环保工作最有成效的五年,即使以今天看,当时环保相关法规的出台之密集,范围之广泛,工作效率之高,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迎接新时代,开启新生活的热情。这五年对产业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在发挥。这五年,中国有了自己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森林法实施细则》、《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实施了5项环境质量标准,36项污染物排放标准和17项环境基础和方法标准。初步建立了环保执法的科学技术规范。也为环保产业的第一次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全国进入了污水厂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到1990年,有150多座污水厂建成投产,各个工业项目也都同步配套了环保设施,无疑为宜兴的环保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而对于宜兴环保产业的最大机遇,竟是我们现在一个又爱又恨的领域——房地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等大城市房地产开发大规模兴起,当时的政策是谁开发谁治理,城市污水处理设备市场需求很大。但是因为整个环保市场并不规范,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标准出台,开发商选择环保产品也只是为了应付政策的要求,而不看重产品的实际应用状况。这样一个现实情况给了高塍环保企业一个加速发展的机会,业务员的作用发展到登峰造极。到了1993年底,仅高塍镇的环保企业就达到了228个,产值也达到了六亿元。但这种资源获取与配置方式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很多企业业务员在外利用拉关系吃回扣的方法销售产品,没有人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与应用,这也让高塍环保产业的发展留下了一个畸形的后遗症。同时,在高利润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市场资源流向脱离集体企业的技术员和业务员手里,集体企业开始出现业绩停滞和亏损现象。
这一年,全国第一个国家级环保科技工业园落户宜兴,“环保产业之乡”声明远播
进入90年代,随着92年小平南巡讲话,“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提速开始了;92年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曲格平领取了联合国颁发的国际环境奖,这是世界范围内环境领域最为崇高的奖项,标志着世界对充满活力与责任感的中国的认可,中国也逐步融入世界秩序,大量的定向贷款,促进中国开始更多的建设环境治理设施,并引入更多的先进技术与资本。时代的印记,投影在宜兴,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两个:“改制”与“合资”。
94年,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思想,宜兴的环保企业进入全面改制阶段,改制工作进行的全面而坚决,集体股份大量退出,“英雄时代”开启,94,95两年,宜兴就完成200多家企业的改制工作。高塍建筑环保设备公司由王盘军正式接掌,当年的销售收入,就从常年徘徊的2000万元,突破到3000万元以上。也是当年,这家宜兴环保产业的“黄埔军校”有了一个新名字—宜兴市鹏鹞环保有限公司,时至今日,仍有40% 的宜兴环保企业,是从鹏鹞出来的人创办的;一名叫陈孝新的明星业务员,他也是王盘军的二儿子——王洪春的高中同学,被领导制定任命为已亏损很久的宜兴市水处理环保设备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后来的故事,和历史上众多明星企业家诞生的方式一样,承担历史债务,接收企业股权,带领企业脱困,陈孝新的公司,也更名为博大水处理有限公司,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时,我们又要提到姜达君,他的弟媳——王腊华,在他的帮助下1984年就自己开办了环保企业,94年,她的公司已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华都绿色集团,也在那一年,她投入178万马克与德国著名企业,有固液分离专家之称的琥珀公司共同开发固液分离技术。从此,“华都琥珀”也在中国享誉南北。
对内改制,与对内合作,又一次极大促进了宜兴环保企业质与量的提升,宜兴环保产业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自己的第一梯队,形成了在中国代表宜兴的环保品牌,1996年,宜兴的环保产业达到顶峰,全国环保产品中,有30%是宜兴生产的,一个小小的江南小城,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产业奇迹。
至90年代末期,中国一直处于经济总量快速发展,固定基础投资快速发展的阶段,虽然那个时间,全国的环保投入仍保持了20%增速,但环保投入占全国GDP的占比始终徘徊在1.5%以下,而国际上的通行的惯例,要达到污染和治理的平衡,至少应保持在3%,同时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较环保投入的速度,可以用一骑绝尘来形容,中国的环境,非但没有完成旧账的清理,反而开始向未来预支,产生了欠账,环境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并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零点行动”,“淮河治理”,“三河三湖”成为这一时期的热门词汇,区域治理逐渐成为了环保事业的主题。
如果说先前的点源控制阶段,成就了环保产业的初期成长;区域治理,就是大资金,高技术,强管理综合集成的大阵仗了;先前的环保产业成长,基本属于自发原生,国家正规的机械,电子和资本力量没有过多介入,是标准的游击队+独立团模式;而进入区域治理时期,国企,外资背景的工程公司,技术公司,设备公司纷纷而来,BOT,TOT,BT等投资方式因为解决国家的资金难题而备受青睐,环保产业,进入大兵团作战时代。宜兴的环保产业,也迎来了最严酷的一场考验,宜兴的环保产业份额,开始出现大幅回落,进入慢进实退的阶段。
不得不感叹,宜兴人敏锐的市场嗅觉和坚韧的品格,还是有一批宜兴人,通过灵活有效的市场网络,准确的捕捉到市场的走向,鹏鹞率先在宜兴成立了设计院,培养了一批设计队伍,并拿到了环保工程甲级资质,再一次走到了市场的前面,没有为大浪扑到,反而挺立潮头,并在2003年,鹏鹞控股的亚洲环保在新加坡主板上市。一批类似鹏鹞的宜兴企业,最终在这场考验中抓住了机会,壮大了自己,形成了今天宜兴的产业格局。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已经很难描述现在中国的情状,但就环境问题来说,已经不是当年大多数人眼中的未来,预言和口号,他突然变得和我们的衣食起居,柴米油盐密不可分,他突然与道德和政治常常被提起,他突然变成了民族希望,支柱产业;环境问题,成了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成了两国争论的敏感词,成了风投眼中的香饽饽。产业之福,国人之祸。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发达国家在长时间逐渐积累和显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显现,集中爆发。城市化的进程,环保产业的需求激增。环境修复,变得火爆非常,对于污染指标,人们观察的多,知道的多,要求的多。中国的环境问题,随着互联网的革命性发展,开始进入公开信息管理阶段;环保产业,也开始进入综合服务与治理时期。
宜兴的环保产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经过了史诗般的起伏跌宕,宜兴仿佛是一个中国环保产业的活化石,保留着各个时期鲜明的历史特征;有好像一杯芳醇艳丽的鸡尾酒,每一层,仍然闪烁着蓬勃的生命力。既有正在转型成为综合服务商,拥有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具备了充分的现代企业特征;也有大量家庭作坊式的设备加工厂,男女老少齐上阵,仿佛改革开放才开始。既有省一级的,由当地企业和著名高校成立的技术研究院,有大量中外合作成立的研究平台;还有大量的业务员,在中国大江南北抢占环保工程;一些公司,甚至将总部设立在北京,聘请业内高手掌柜经理,而在大部分公司,业务员文化仍然大行其道。大家都在观察,宜兴,能否像当年那样,重新承担起新时期的历史使命。
在整个民族都在宣扬环保的今天,在万物必谈环保,谈环保必谈宜兴的今天,这座城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亚于当年那场2800元的技术鉴定会。
中国,在等待宜兴新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