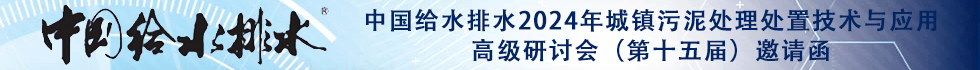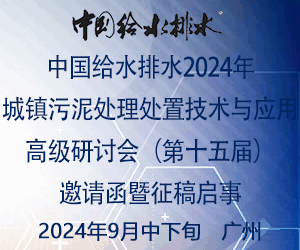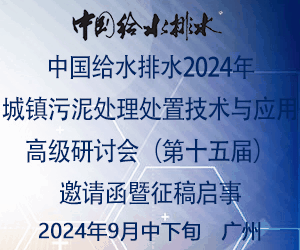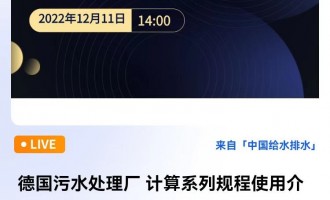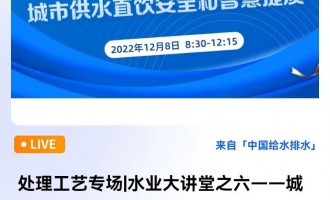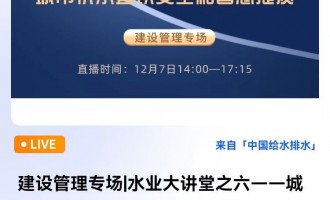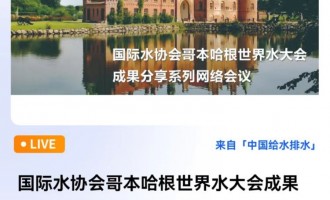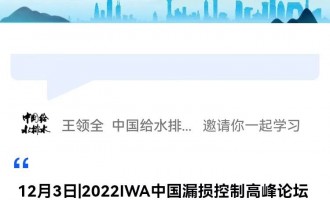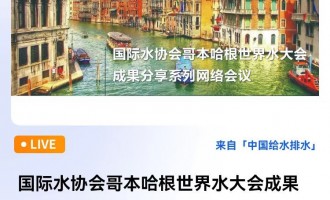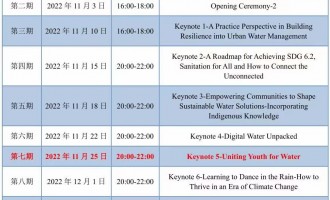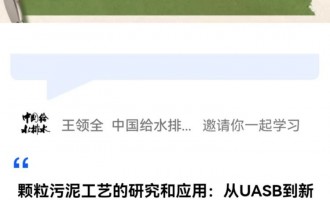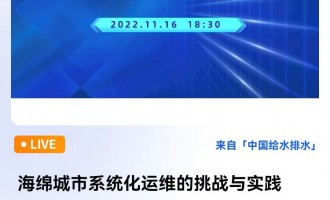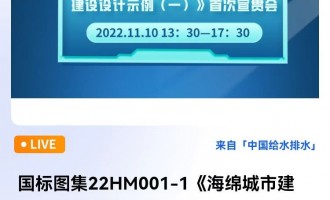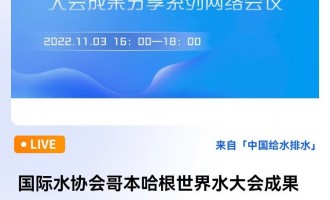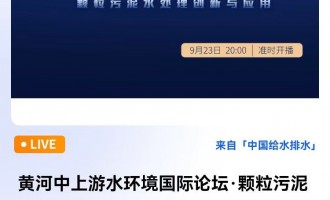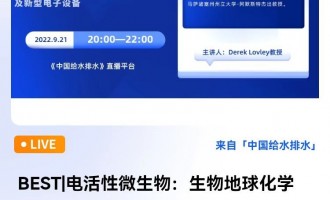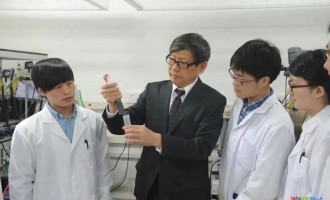6、规划与可持续投资
规划问题在于由谁来主导水务规划。表面上看,规划由政府主导,天经地义,但是需要水务企业具体推动规划的实施和细化。特别是当地的国有垄断的水务企业,长期经营,对当地的情况,如各类地下管网的布局、用户的真实需要求以及制水厂和污水厂设置等问题比政府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现在应用大数据系统,企业在规划上的能力更加具有优势。正是由于企业是经营主体,在规划时还要考虑经济平衡,还要进行投融资规划、实施和资产管理计划,这样就避免了重复投资和低效投资。同时从规划入手,不仅仅降低投资建设成本,还会降低运营成本,这样使自身的投融资能够进入可持续的轨道。当然,水务企业的规划最后还是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但经过这样流程实施的规划效果、效率和效益会大大提高。
7、体制与机制
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是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的基础。水务改革确实要重新理顺行业的体制,完善机制。体制是指各方关系,机制是指运行的动力、流程和路径。水务企业的定位不清楚,地位行业不清楚,到底和政府什么关系,和老百姓什么关系,都要重新梳理一遍。需要从制度上明确政府和水务企业的职责边界,这样企业才能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要建立水务的特许经营制度,每个地方都要有。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社会资本,要通过特许经营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约束不规范行为。并且通过重新修订供排水条例来确立政府、企业和用户的三方关系。为什么要重新修订条例,因为把很多条例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制定的,供排水业务中很多东西当时还没有,例如二次供水、价格听证、污水处理费等。在认识到公共治理重要性的今天,再也不能让水务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法律不完备的环境下进行了。
机制的作用除了业务流程、规范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发挥激励的作用。一个敏感的话题是,国有垄断的水务企业的管理层及员工应不应该按照市场水平给予薪酬激励?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肯定的原因是这些国有企业的保障和提高效率的任务很重,确实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达到目标就应该奖赏。如果不奖励,全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大。否定的原因是水务企业确实是在垄断的基础上获得的利益,效率提高引起的成本降低应该让老百姓分享,而不能仅仅用于管理层激励,这就需要机制设计与平衡。
另外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是定价。国际上一般有两种定价方式,一种是固定价格或固定成本,另一种是成本加成。这两种方式给出的激励效果是不同的。固定价格或固定成本是把企业的利润空间都放在里面,一口价,这样企业为了提高利润就会不断主动降低成本,当然要满足服务质量。成本加成就会使企业不断放大成本,躺在政府身上,甚至可以不要那个“成”,自己也不会降低成本,所以需要成本规制。去年国家发改委提出到2020年建成“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定价机制就是这个意思。
8、水资源一体化管理
最后不得不提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水资源浪费比较严重的国家。“每年损失一个太湖”。水资源被分割管理,不仅多龙治水,还多龙用水。在水资源的共治共管就等于无人管理。在强调“绿水青山”的今天,更加要形成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地方水务企业就要发挥关键性、引领性的作用。水务企业不仅要制水,还要用技术手段、管理手段甚至是行政手段进行治水与管水。水务一体化,不仅仅是将供水和排水放在一个篮子里,还要做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另外,随着我国开始进入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一体化,那么流域一体化管理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大型水务企业能否参与流域一体化的管理与运行,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重大问题。
三、水务改革的曲折进行时:以上海为例
二十多年前,上海就启动了水务改革。上海不仅仅是中国水业的先驱,还是中国水务改革的先驱。一百三十多年前,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自来水厂——上海杨树浦自来水厂就在上海诞生。仅仅是这家厂,现在看来,还诞生了几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第一”。她居然还是个外商独资,具有特许经营协议的PPP项目,还是个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IPO项目。1922年,上海还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东区污水处理厂,仅仅比全世界第一个污水处理厂(1921)晚了一年。这两个水厂目前还在正常运行中。杨树浦水厂的主体建筑群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堡式建筑,这在英国也几乎找不到了,所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许也可以列为第一。在水务PPP方面,上海也创造了几个第一,率先作了水厂的BOT项目,即上海大场自来水厂(1996),几乎与成都自来水六厂B厂同时。上海率先进行大体量的污水处理厂的BOT招商(竹园一厂、二厂170+50万吨/日)。更重要的是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在中国第一个带管网运营的系统性PPP项目,从而带动整个中国水务等市场化进程。下面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上海水务改革的历程和可能的前景。
1、上海水务改革的历程
上海的供水行业是从1999年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是在1993年,为了筹集上海水源地建设资金,趁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成立,公开发行原水公司股票。之后不久,上海凌桥水厂建设也公开发行股票,用上市公司的方式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上海又是第一个。1996年,上海出台《供水条例》。在当年上海大场自来水厂BOT项目完成招商之后,上海水务部门一度认为可以厂网分离,厂独立结算,走市场化道路。但是试行一年之后,又发现各种问题,最重要的是成本居高不下,又将厂网合并至上海自来水公司。而此时上海财政又要每年拿出8亿元用于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压力较大(还有公交,煤气)。
为了响应整个上海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1999年,上海自来水公司一拆为四,分为市北、市南、闵行和浦东四个公司,分而治之,希望这四个公司进行成本比较竞争,同时调整水价,政府不再补贴,确定供水为经营性行业。2002年,完成浦东自来水国际招商,引入法国威立雅。2005年,这四家自来水公司整建制(包括浦东50%股权)划入上海城投总公司。2008年调整水价。2011年,上海最大的水源地青草沙水库建成投运。2011年,上海市水务局出台《供水成本公开实施意见办法》。2013年出台《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同时完成新一轮水价调整。2014年伴随上海城投总公司改制成上海城投集团,四家自来水公司包括原水公司和排水公司组建成上海城投水务集团(之前闵行与市南自来水公司合并)。
编辑:赵凡
第2页 /(共2页)
排水改革的历程也很有特色和国际范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上海水环境(包括苏州河黑臭)始终存在各类问题,包括内涝、生活污水冒溢和管网严重不足,上海就考虑用世界银行资金建设排水基础设施。世界银行经过调研分别给出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解决方案。技术上用雨污合流制、长距离集中运输,集中处理的方式,并构建三个污水处理片区。在经济上,建立排水市场化公司化运作的体制,建设利用世行贷款,还款利用向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征收排水费的方式。为了顺应世行贷款的要求,1992年,上海市将事业单位排水处加挂上海市排水公司的牌子,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并开始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合流一期工程,同时开始向企事业单位征收排水费,这是国内第一次。
经过3-4年的合作,世行发现这样的改革不彻底,没有按照他们市场化运作的要求,特别是排水公司本质上还是事业单位,世行对事业单位的财务报表看不懂,继而要求上海市将排水公司改为有限公司。于是,1996年排水公司转为上海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同时要求出台《排水条例》,在条例中明确排水公司的法定地位;国内第一次向普通居民户征收排水费,并将排水费从行政事业性收费改为经营性收费。由排水公司作为征收主体,自收自支。这样,世行的用款和还款有了保障。可以说,是世行推动建立了上海排水市场化的运行体制。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体制,世行贷款、用户付费,再加上一些上海财政的补贴,基本上解决了上海排水设施早期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上海也成了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排水费经营性收费的城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体制,上海排水建设有了充分的资金,基本建成了自身的排水设施系统性骨架,也使上海总体上消除了污水冒溢和城市内涝。
1999年,上海为了治理苏州河黑臭问题,也是用世行贷款提高了排水费。2002年,竹园污水处理厂BOT项目招商成功。2005年,为了建设合流二期和污水三期工程又提高了排水费,2008年增加了政府财政补贴。随着上海市政府对城市水环境和防汛的要求提高,排水设施建设规模加大,速度加快,原有的世行贷款+用户付费+政府少量补贴的融资框架已经出现较大缺口。即使是政府在建设中提高财政出资比例,但是反过来更加增加排水公司的运营成本。2012年前后,排水公司开始出现亏损。2014年,上海排水公司并入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完成供排水一体化改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几乎在同时出台《城镇排水和污水管理条例》和《污水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为了顺应政策法规,2015年,上海将排水费从经营性收费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市排水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订《排水服务政府购买协议》。2016年,排水公司的亏损状况开始得到好转。
2、上海水务改革可能的前景
纵观上海的水务改革,可以说,市政府还是高瞻远瞩,并且还是有国际格局和不凡勇气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改革,上海的水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不断走向更高的台阶。
回看整个二十年,上海的水务改革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96-2005年,改革促进建设;2、2005-2014年,改革与建设相辅相成;3、2014-至今,建设先于改革。近年来,上海水务和水环境的重大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但体制机制的改革出现了相对滞后,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在:
重新修订《供水条例》。《供水条例》自从1996年出台以来,经过二十年没有修订,而上海市的供水投资建设和运营内外环境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供水条例》需要明确政府、公众和企业的关系。
建立供水特许经营制度。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一直想通过建立供水特许经营制度,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职责边界和企业的成本边界,提高供水企业的经营效率。
理顺供水价格体系、定价机制和成本监审机制。国家改委和上海市发改委都出台了包括水务在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的“准许成本+合理利润”的价格体系。上海要完善这一价格体系,明确准许成本,建立固定的定价机制,细化成本监审的工作规则和内容,建立上海供水经济监管体系。
完善排水定价机制和支付机制。现在上海排水费改为污水处理费,并调整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除了还是要完善排水污染者付费的定价机制上,以免未来政府财政压力过大以外,可以考虑在支付机制上优化调整,以更好的支付机制来激励排水公司提高效率。
四、当下的措施和未来的路
对任何地方和城市而言,水务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改不行,否则当地的水务建设与运营玩不转。用PPP来代替水务改革更加不行,相当于用镇痛膏治疗风湿病。所以,各地政府应该下定决心,立足改革,打造隶属于自身的水务子弟兵,最终做优作强,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优质的水务服务。
水务改革具有系统性、阶段性、战略性和外部性的特征,其潜在的效应应该是在扎实工作以后慢慢发挥出来的。所以要想好当下采取什么措施来止血,来强身健体以及未来的路。先设想好未来的当地水务服务的图景,然后规划好水务企业应该达到的能力,最后设计好水务改革的路径。
根据上述讨论,当下的措施可以设计成遵循国家政策,形成水价定价机制,完改善本地国有水务企业现金流,恢复和提高融资能力,给与本地国有企业政策与项目支持,使企业能力迅速提高。未来的路包括建立监管,特别是经济监管平台和体系,建立特许经营制度,促进企业主动提高效率,完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水务改革的基本套路。
本文作者/王强
中国水网金牌专栏作家
现就职于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00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巴特列特研究生院建筑经济与管理专业(主修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和PPP/PFI)学习并获理学硕士学位。2005年加入上海城投以后,牵头开展了《基础设施投资新趋势-上海PPP模式研究》并于2010年获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奖,此研究被上海市法制办誉为“上海市特许经营立法的理论基础”。2006-2007年参与了《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并向上海市政府立法相关部门系统性地提出建议并大部分得到采纳与吸收。作为上海城投项目小组成员,参与了数个上海市重要的PPP项目的重组和政策制定工作。2007年,发表经济监管体制研究,对完善中国的水业监管有较大借鉴价值。2009年,牵头上海城投投资的BOT项目上海长江隧桥的通行费征收方案的研究,成果得到上海市政府批准并实施至今。他先后又参与了上海市市级层面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绝大多数的研究工作,如《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实施战略研究》,该项研究与2012年被国家发改委授予优秀研究成果奖。2013年王强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世界银行报告《城市水务事业的公私合作: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述评》。2015年4月中标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上海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深化研究》。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十九大中,“两山论”被写入党章,环境产业成为“两山论”落地的中坚力量。
4月2日,由E20环境平台主办的“2018(第十六届)水业战略论坛”在京启幕。站在改革新起点,纵深发展20年的水业将如何把改革进行到底?
黄金二十年,环保走向“大生态”
从1998年到2018年的纵深20年,在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发改委、财政部PPP双库定向邀请专家薛涛看来,水务发展是一个“水大鱼大”的发展过程,在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之下,从摸着石头过河、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发布,市场化大刀阔斧地改革,到大资本时代加速,直至PPP成熟潮,水业发展“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E20研究院院长傅涛认为,政策为环保产业插上了翅膀。傅涛在论坛上指出,政治是环境市场之本,“两山论”赋予了环境产业新的使命,环保产业要以政治挂帅,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文明的改变是价值观的改变,两山产业的兴起,是产业价值链的上移。如果生态文明是一栋房子,两山经济就是顶梁柱。”
与此同时,产融结合助力水业发展腾飞。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财政部入库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952个PPP项目中,涉及水环境综合治理的PPP项目总数已达到755个,占比近80%,项目金额总计超过9000亿元。

环保产业正在从环保走向大生态。“十三五”及“水十条”出台之后,传统“末端治理”模式正在向“全流域治理”推进,全流域一体化生态单元的运营,将在水域生态在线监测、水污染应急预警方面产生极大的需求。水污染治理“由点及面”,从过去的点源控制走向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在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环保及公用事业首席分析师邵琳琳看来,将来水务行业市场空间巨大,机遇集中于三个方面:水环境综合治理继续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市场启动,以及污水处理厂推进提标改造。
在水环境综合治理方面,水务企业、环保企业在未来的大生态产业中,竞争的同时谋求联盟式的共同发展。此外,据E20研究院统计,目前建制镇污水处理率为30%,村污水处理率不足20%,后续市场启动空间大。最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至地表IV甚至III类水将会逐步得到推进。
痛点依存,如何将改革进行到底?
走过漫漫20年的改革路,水环境治理市场蓬勃发展。但在发展路途中,仍面临“拦路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资源能源所所长、住房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家卓在论坛上直指水业当前面临的困局与挑战。
第一,重厂轻网,污水收集系统效率低下,进水浓度低。王家卓指出,过去对管网重视的欠缺,导致当前污水收集系统效率低下、进水浓度低。数据显示,2007-2017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数量和处置规模不断增长,从1148座增长至4802座,总处理规模从7554万吨/日增长至18558万吨/日。
但反观2017年各省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COD浓度(mg/L)不升反降。全国31个省市,进水平均COD浓度低于350mg/L的有24个,以低标准测量,低于150mg/L的还有4个。观察2007-2017的十年间平均进水浓度COD发现,污水处理厂容量的增大并没有转化为处理能力的提升,经过大比例稀释以后的污水、河水、地下水、山泉水等和污水混在一起进入了污水处理厂,而这不仅挤占了污水管网的收集能力,也挤占了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浪费了地方政府大量污水处理费用。
而症结在于政府不重视、设计不科学、材料不合格(管网质量差)、施工不规范、人员不到位、管理不及时。
其次,排水体制混乱,合流分流说不清楚也是阻碍改革道路上的一道坎。王家卓直言,各城市早期建立的排水系统基本都是合流制的,合流制并非水环境差的“罪魁祸首”,合流制分流制互有优势,但是我国有些地区过于强调雨污分流。“黑臭水体的罪魁祸首在于没有控制的合流制污水雨天溢流,导致水污染;分流制地区的雨污水混错接严重,尤其是污水接入雨水管,导致旱天直接排放入河”。
除以上挑战外,部分地区控源截污做得不到位、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力度欠缺、生态环境生态修复表面化、虚无化,把生态修复异化成种水草、撒药、铺石子、曝气,以及盲目追求大水面高水位,导致河水倒灌进水排水管网,且增大排涝压力等都是发展道路中亟待破解的重重困局。
还需关注的是,水环境治理存在五千亿资金缺口,薛涛在论坛中指出,财政部强调降杠杆的情况下,已逼近PPP的天花板。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未来已来,水业乃至环保产业,还需直面困局,对人民群众的环境诉求当仁不让,将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