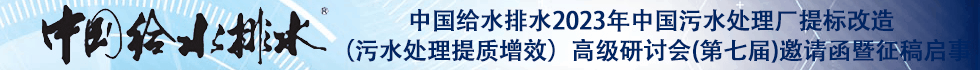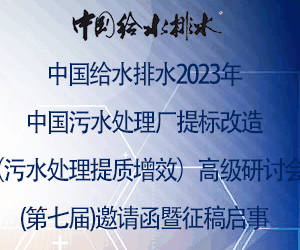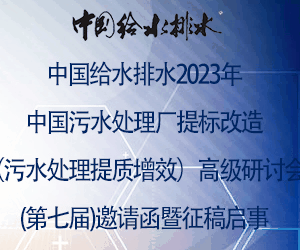“河长+检察长”制度创新与实践探索
时间:2020-09-18
来源:检察日报
●“河长+检察长”这种协作机制尝试通过纳入检察机关的司法作用,来进一步提升“河长制”在河湖系统保护和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方面的效用发挥。
●目前,“河长+检察长”的治理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广泛推广,拓宽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来源,提升了检察监督的效能。
●跨区域司法大数据共享、分析和应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如何协调生态环境资源损害行为地和结果发生地的办案诉求差异等,都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伴随公共治理的深化,对环境利益的维护在我国被予以突出强调。传统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味追求GDP增长的公共治理路径以及生态环境系统自身的高度复杂,都成为掣肘环境治理迅速、有效推行的因素。也是在此背景下,“河长制”被作为地方环境治理的创新模式获得广泛推广。
“河长制”最初因太湖蓝藻事件而在江苏发端,后被作为有益经验而在全国推广。这种制度的要点在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河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主要河湖设立河长,由省级负责人担任;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均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负责人担任。各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尤其是河流治理的规划编制、督促和落实人员、项目以及资金的到位。“河长制”之所以取得显著效果的原因在于:其一,它将环境治理尤其是河流治理的目标和责任细致落实到了地区行政首长身上,既确保了环境治理的权威性,也使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被切实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其二,它有效促成了河流水域的协同共治,这种协同共治不仅含括不同地区,也含括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动。因为省级政府首长作为总河长,而不同级别的政府首长和涉水各部门负责人担任不同层级的“河长”,地区和部门冲突通过联席会议予以协调和解决,由此也促成了水环境跨流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其三,它还创新性地引入了地方在环境治理上的“党政同责”机制,即党委主要领导同样需作为河长承担生态治理责任。
“河长制”获得广泛推广后,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河长+检察长”的升级版协作机制。与此前的“河长制”相比,这种协作机制尝试通过纳入检察机关的司法作用,来进一步提升“河长制”在河湖系统保护和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方面的效用发挥。而其基础又是借助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各级河长办公室与检察机关联合印发的有关协作机制如何展开的指导性意见中,协同领导、信息共享、办案协作、联合工作、日常联络等工作方式被作为协作机制的具体展开形式渐渐形塑出来。所谓协同领导,即各级河长与检察长对水域治理的重点工作和重点案件,通过联合巡查、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协同领导、统筹规划;而信息共享和办案协作则强调双方在案件线索、巡查结果和整改反馈等方面都应互相沟通、双向移送;联合工作、日常联络也旨在确保这种协同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河长+检察长”的治理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广泛推广,被认为拓宽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来源,且提升了检察监督的效能。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一直以来都是检察机关强化行政公益诉讼的重点范畴。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也同样意味着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应承担的积极职责,它与检察机关对于生态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追究以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起,成为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方面所应承担的积极司法保障职能。
与其他的检察公益诉讼相比,建立“河长+检察长”制度之后的环境检察公益诉讼表现出如下特点和优势:其一,它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与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予以有效整合。检察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意味着,当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项前置程序设置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被提起之前,为行政机关提供再次履职的机会,由此保障程序经济和节约司法资源。但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前置程序的运用本质上还有尽早完成环境修复,避免污染扩大的考虑。这一点也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实践”在近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中被予以特别强调的背景,而“河长+检察长”的有效联动、协作办案也被证明,能够有效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恢复性司法的难题;其二,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机关上下一体推动。“河长制”所调动的主要是行政资源和行政系统,此外还主要通过“党政同责”将各级党组织纳入生态环境的治理体系。“河长+检察长”制度则在此基础上纳入了司法系统,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司法责任与司法保护,由此也使生态环境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更加完备;其三,这种创新性制度的出现也同样推进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塑成与细化。我国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确立时间尚短,制度也仅是初具端倪,因此需结合各个领域的具体实践进行形塑和磨砺。而“河长+检察长”制度的实践恰好为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塑成提供了场域和基础。在推行这种协作制的过程中,最高检曾出台《关于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明确跨省案件统一管辖和线索移送等五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为解决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鉴定难、费用高的问题,最高检还增加环境资源领域专业鉴定机构,推出检察公益诉讼中不预收鉴定费的鉴定机构。此外,各地检察机关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建立台账、拉条挂账、整改销号”等独具特色的制度,形成符合本地方特点的环境治理手段,并推进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的集中治理。而在检察系统内部,同样针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扩散性特点而进行跨省域的检察协作与检察保护,例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市检察机关共建的赤水河、乌江流域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机制。上述制度创新都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持续推进和制度提升提供基础。
但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遇实施困难,也需要在化解与克服困难时再反复进行制度整饬与调试。从目前既有的“河长+检察长”制度的实践来看,这一制度的有效运作同样遭遇如下问题:其一,行政与司法的协作尚未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下具体形成。尽管“河长+检察长”制度的核心在于行政与司法的协作机制,但目前实践中的这种协作只是通过联合巡查、联席会议等工作联络方面展开,并未形成有利于环境检察公益诉讼有效开展的具体制度。也因此制度化水平不够,行政与司法的协作就常常出现协作不深入、信息共享不及时、联动办案不紧密等问题,也常常流于协作的形式;其二,在检察系统内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被作为生态检察工作的重要一环予以强调,检察系统也着力于促成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为主导,民事检察、行政检察为补充的基本格局,但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如何有效衔接,尤其是与行政公益诉讼如何衔接,目前同样未达成制度性共识和统一处理方式;其三,无论是“河长制”还是“河长+检察长”制度,都根据环境治理的跨区域特点,着眼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机制。但相比行政系统内部的跨区域协作,跨区域检察办案却遭遇很多制度性障碍。例如,跨区域司法大数据共享、分析和应用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对跨省市环境犯罪和违法的空间分布和转移态势进行细致分析、联合发布数据分析报告,形成共管共治等机制尚不健全,跨省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由哪个检察机关具体提起,如何协调生态环境资源损害行为地和结果发生地的办案诉求差异等,都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其四,完整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不可缺失的一环是由法院来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进行审查,但目前的“河长+检察长”制度因为重点在于塑成行政与检察的协作,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未充分考虑法院的司法审判体制,这就导致某些创新性制度,例如跨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检察机制与法院对于环境类案件的集中管辖之间相互抵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所欲追求的整体化和系统性目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河长+检察长”制度的创新虽然在实践中带来积极成效,却也需要不断进行实践磨砺和制度调试。